

“块茎”是什么
戴米安·萨顿 大卫·马丁-琼斯丨文
林何丨译
选自《德勒兹眼中的艺术》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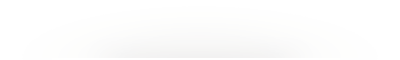
“块茎”本指一种植物茎,可在地下水平延伸、生根发芽。很多禾本科植物具有块茎,我们日常饮食中用到的一些普通植物,像芦笋、生姜、马铃薯等,就是如此。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他们的著作《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1980)的前言中,使用这个词来描绘一种思维方式。他们认为,水平延伸的块茎上生根发芽这一形象,可以概括他们所青睐的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超越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法。后者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以因果关系、等级体系、二元结构(一/多、我们/他们、男性/女性等)为特点,统治西方社会已达数千年之久。
由于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思维模式强调因果关系,制造种种等级体系,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其比作树。一是因为树本身实际的形象(种子为因,树为果);二是因其可以象征谱系结构,例如,它可以表达一种认祖归宗式的族谱结构,反映包括单一源点(父亲)与其后嗣之间清晰的因果关系。因此,树的形象表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想模式创造了单一的真理(可理解为一棵好像是单独存在的树,当然也可理解为一位父亲、一个家庭),然后以此定义“他者”(以区别出树的周围空间或可称之为“不是树”的部分)。虽然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1844-1900)已经指明了另外一种思想方法的方向,但这种二元思维模式由来已久,至今仍占据优势。深受尼采的影响(德勒兹曾于1962年写出《尼采与哲学》),德勒兹和瓜塔里一道发展出了块茎思想。
但德勒兹和瓜塔里建立的块茎思想,并非要对抗西方主导思想,绝不是树与块茎的简单对决。倘若如此,只会创造出又一个二元区分(区分敦是敦非),这恰就暗合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打算重新思考的西方主导思维模式。相反,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块茎的形象的确暗示要“取代”树的形象,但德勒兹和瓜塔里试图说明,块茎思想不是一种对抗式思维模式,它并不打算一统天下。将树放至森林中来理解,也许才是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异的最佳途径。森林中没有单一真实,没有单一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唯一的“真实的”(true)树。森林是由无数的树或者无数的“真实”(truth)组成的单一实体。不能仅仅因为可能无法判定哪棵树最早出现,就为森林假定一个起源。任何树都是群落、水、阳光和土的创造物。倘无这些条件,即便有种子也无法长成树。因为事物是由诸多不同要素构成的组合关系所生成的,并不存在单一的起因,因此不能将树看成单独的存在。就此而言,任何事物都是块茎,树的思维模式充其量只是使用了块茎的一个方面而已。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我们不应该总是把事物简化为“一个事物和它的诸多他者”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真实的思考方式和其他诸多与之相竞争的思考方式之间的关系,相反,我们应该认为每个事物总是已经包含了许多真实。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认为树的思维所体现出来的等级结构形象不切实际,应加以抛弃,代之以块茎的水平延伸形象。不是树,而是块茎;不是一,而由多组成的一;不是一和多重他者的关系,而是单一的多重性。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就像森林一样,块茎“既无开端,也无终结,只有中间状态(环境),它从中生长,又蔓延开去”。
一些具体实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块茎那庞大的分叉和块茎式思维。德勒兹和瓜塔里曾用块茎来描述生命实体(群居动物,如老鼠、狼),也描述像地穴这样的地理实体,描述“其在栖居、储藏、移动、躲避、逃脱等各方面的功能”。以群居动物为例,移动的动物群持续不断地形成和再形成一个单一的形态,这是一个流动的实体,它既是一也是多。一群野马,一群盘旋的飞鸟,就是块茎思想很好的例子。地穴,则为我们思考块茎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视角。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越共曾使用游击战术对抗在军事技术上处于压倒性优势的美国军队。作为战斗的一部分,他们使用了一种复杂的地道系统,他们凭此能躲避美军地面和空中的火力,并能储存和传送武器,得到补给,能建造暗堡进行伏击和避空袭,一旦被包围还能迅速脱身。……
在此,需要提醒读者,一旦我们用块茎思维来理解思想(或其他任何事物),总会有一种深深的不确定之感。块茎有制造巨变的潜能,或者用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所使用的术语来说,有解域(deterritorialise)的潜力。但同时,还有一种互补性变动,总是涉及一种企图重新创造稳定和秩序的力量,去再建域(reterritorialise)。块茎是一种变化的形态(不管是鸟群迅速变换的阵形,还是森林缓慢的扩展),它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逃逸线”(line of fight),从而实现解域。沿着逃逸线,块茎就有潜力进入(和迈上)新域。逃逸线来自块茎形态的边缘,在这里多元性体验到一种外在性,然后发生变形和改变。这一边缘存在着双重的生成,既改变块茎,也改变块茎所面临的事物(实际上,块茎面临的总是另一个块茎的边界)。德勒兹和瓜塔里以黄蜂为兰花授粉为例来解释这一进程:
解域的运动和再建域的进程怎能不相互关联、不断联结、彼此牵涉?通过追踪一只黄蜂的形象,一株兰花得以解域;靠这一形象,黄蜂得以再建域。然而黄蜂同时也被解域,因为它自身已变为兰花繁殖器官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传播花粉,黄蜂又使兰花再建域。作为异质的兰花和黄蜂最终形成了块茎。
这个例子表明任何解域都会伴随着再建域。当遇到黄蜂,兰花就不再完全是兰花,它就会发生解域(即生成黄蜂的过程),但由于花粉被黄蜂带至别处,它也发生再建域。这一过程反过来,就是黄蜂的解域和再建域。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兰花的生成-黄蜂,黄蜂的生成-兰花,每种生成都促成了一方的解域和另一方的再建域。”所有这样的相遇创造一种聚合(assemblage)现象,而聚合的两种事物之间则产生双重生成。
然而,这个例子没能直接展示这种相遇通常伴有的权力不均衡情况。要想更清楚地展现解域和再建域伴有的不确定性,值得考虑一下人类最具暴力性也最有影响性的解域和再建域形式:殖民统治。当美洲这个“新大陆”被欧洲人首次正式“发现”时(更不用说后来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它的海岸线最初由水手探索。随着这些土地逐步被欧洲移民占有,土地的殖民探索也就开始了。这些探索既是欧洲身份的解域,因为他们在欧洲之外开拓了新领土,也是一种再建域,因为他们开始在新的土地上定居。这一探索的过程内含了一种生成的相互过程:殖民者适应新土地,新土地适应殖民者。经过与新土地和土著的接触,欧洲文化的价值观和习俗被解域、变形,最终以新的形态再建域。同样,由于陌生者的出现,这些土地上的土著(实际上也包括土地本身)也被解域、再建域,最后变成新的形态。
但是,殖民史是一部不均衡再建域的历史。尽管强势的欧洲文化尽力适应所面对的新土地和族群,但最终还是将自身强加于新大陆之上。如果认为战争、屠杀、种族灭绝、奴役、集中营、赋税、土地清理、疾病以及其他无数这样的伤害行为仅仅是“再建域”,那就过于委婉了。强势的殖民力量与另一弱势的块茎相遇,前者通常发生变化,而后者却往往被前者的文化所吞噬或强行再建域。这样,尽管块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但是,由于相互生成-他者的解域和再建域过程中的不均衡现象,不能将块茎看成解决所有树状思维模式问题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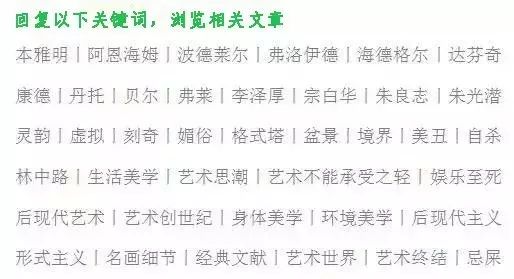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