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8日(周二)下午6点,中间美术馆和AP Project将联合举办第五次中间读书会,主题是“后现代主义“,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本期推送是本次读书会阅读文献之一,阿基莱·伯尼托·奥利瓦(Achille Bonito Oliva)于1979年所写的《意大利“超前卫艺术”》。本篇文章由实习生韦淇翻译。
本篇文章作者阿基莱·伯尼托·奥利瓦是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超前卫”运动("Transavanguardia")的重要组织者。他曾在1993年担任威尼斯双年展 (the 45th Venice Bieannale)的策展人,邀请王广义、张培力、耿建翌、徐冰、刘炜、方力钧、喻红、冯梦波、王友身、余友涵、李山、孙良、王子卫和宋海冬等14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展,让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有了向世界进行自我展示的机会,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置身于全球化语境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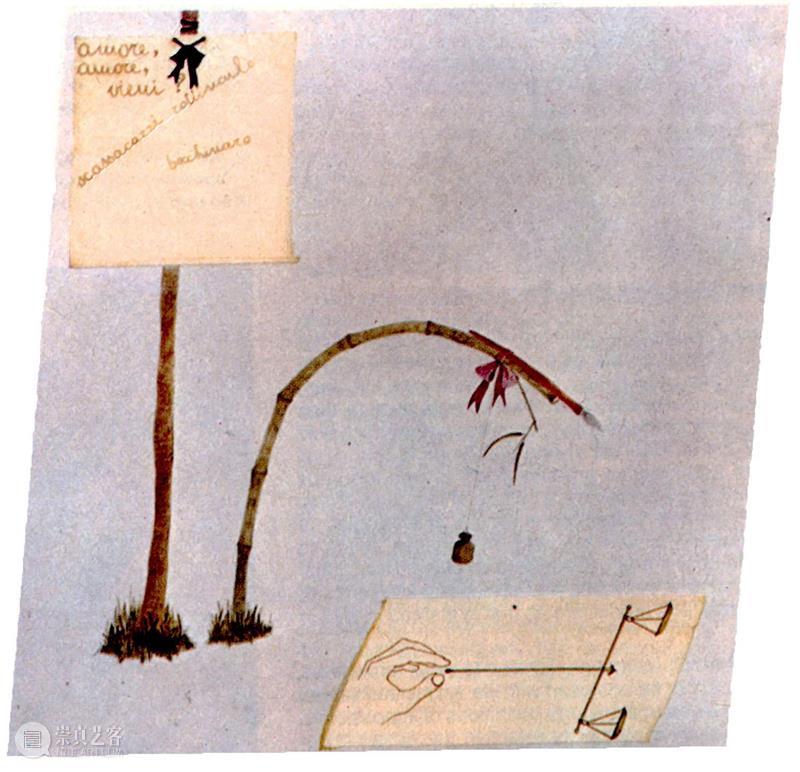
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 “Parole Amorose” (1975),图片来自于原文
终于,艺术回归了它的内部动机即作品形成的原因,迷宫,即“内在机制”,即对作品实质的持续发掘。1970年代的艺术理念是:在艺术中,严格地说,是在游离与悬置的个人意象的实质中,重新发现动手的乐趣与危险。作品成为流浪者的地图,记录着未由任何艺术家预设方向的发展的运动。那些艺术家只是一群视而不见的人,摇着尾巴享受艺术的乐趣,但那乐趣不为任何事物停留,也并不关注历史。
包括前卫艺术在内的1960年代艺术包含了一种伦理观:在意大利贫穷艺术运动的程式中,其核心设计追求一种专制、受虐式的线条,但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并未采用这种风格。随后,艺术实践抛弃了艺术创造中的审查,转而青睐铺张的实践,作为对起初贫瘠(指贫穷艺术运动)的补偿。但作为一种切入口,这种起初贫瘠并非意味着禁欲主义和对物质生活的摒弃,而是成为所有者的能力,因为作品与艺术家受到的剥夺和阻碍,使得物质受限被放置在持续的争议之中。
这种铺张主要体现在它能够在长期不为人知的状态下补充这种初期贫瘠,承担将艺术带入主流的风险。终于,图像实践作为一种积极的运动被拾起,不再是一种抵抗的姿态,而是积极的、日间的、流动的渗透。
起初,艺术是一种灾难的成果,是一种非连贯性,摧毁语言的平衡,以实现对个人意象实质的沉淀。这不是怀旧,也并非回流,而是一种将诸多事物的沉淀一同拽进自身内部的流动,超越了对私人化、象征性的简单回归。
根据定义,前卫艺术向来在一种理想主义传统的文化模式下运作,而这种传统倾向于把艺术的发展塑造为一条持续前进的直线。由这种思想方法衍生的意识形态就是“语言学的达尔文主义”,这种艺术进化理念将语言发展中的传统移植到艺术中,贯穿了从前卫艺术先驱到艺术研究的最新成果。这种立场是理想主义的,其对艺术的考量及其发展与历史沉浮割裂开来,似乎脱离了历史和时代背景。
直到70年代,前卫艺术依然保持着这种心态,在“语言学达尔文主义”的哲学理论中运作,以一种纯粹主义和清教徒式的谨小慎微尊重每一个谱系的文化进化。这导致后来的艺术与批判性创作小心翼翼,以免落入窠臼,受制于连贯性。新前卫艺术的最终目标,是试图在保持作品内部一致性的基础上,在语言的实验性内拯救艺术家“快乐的道德”(happy conscience),对抗世界消极的不连贯性。
这一理论产生了新的胁迫,形成 60年代艺术创作的特征,亦即受困于语言。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这一胁迫使新的技法和方法论显得尤为必要,这一阶段的艺术创作自身的创造能力和思想发展趋势都是具有实验性的。
从70年代开始,艺术家创作中面临的胁迫变成了新的停滞。新的经济制度要求生产的减速。世界被卷入一系列危机,撕碎了一切关于意识形态体系高生产力的幻觉。最终,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愈加激烈,至今仍被视为艺术的一项危机。不过,根据词源,“危机”(crisis)一词同时具有“突破点”和“验证”的含义,那么,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词中发现一种屡试不爽的方法,来验证艺术的本质。在艺术中,对“危机”的定义包含两个层面:艺术之死和艺术进化的危机。
不过,根据黑格尔的术语,艺术之死是指通过哲学,这一吸收了艺术直觉的思维科学,来超越艺术门类。最近,艺术之死指的是人们意识到,艺术体验不再能映射现实的诸多层面。一方面,上层建筑(即艺术)的无力在基础结构(经济、政治)面前的无能为力得到了强调;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艺术创造的水平会下降,从价值沦为价格。
如今,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艺术的危机指的是艺术语言演变的危机——前卫艺术中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认知的危机。由于缺乏新的可操作性,这一关键时刻被70年代的艺术家推翻。他们揭示了艺术的价值,证明在世界的永恒性面前,艺术并非是为了进步而进步,而是在自身和被抑制的内在演化中实现一种有关意识的进步性。
矛盾的是,当今艺术受人诟病的点在于缺乏新意,缺乏令观者时而血脉偾张、时而沉静舒缓的能力。只有当市场需求同质不同样的商品时,“新”才会诞生。从这种意义上说,许多诗人及其相关亚文化团体都被埋葬在了60年代,因为有过多的艺术家从事同一方向的工作,导致“品味”这一概念的形成,从而允许了针对艺术的社会与经济消费。
最终,由于每位艺术家都在进行单独的研究,粉碎社会品味、追求作品本身的完成度,诗性被削弱了。个体性和独立工作的价值与极权体制、政治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和科学叠加交织的社会制度是相悖的,这些会消解现实前进过程中在他们自己的观点和项目内部产生的矛盾和转向。在这样一个集中营里,自身扩张被消减,一切欲望和物质生产中的痛苦和折磨被稀释掉,有预见性的文化必须有所节制。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和科学假说的系统倾向于将所有异类转化为对自身有用的东西,将一切根植于现实中的东西回收并转化为功能性、生产性的条件。
其中不能简化为这些条件的就是艺术,它无法与生活混淆。相反,艺术致力于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性指的就是将艺术创造力与个人生产项目绑定的可能性。在一种外观日新月异但实质从未变更的冲动下,1970年代的艺术家正在研究一种无法被还原为现实的语言。在这种意义上,艺术是一种生命活动,一种应用式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形象大受欢迎而内在无人问津。艺术是无法交易的,艺术家需要将当下的创造变得确切,但又需要创造运动中的不连贯性。同时,具有生产力的概念存在着严格的不动性。
如今,艺术不是艺术家在语言领域内发表的评论,它与现实并非二元或镜像关系。在这种意义上,1970年代的艺术生产发展道路需要其他学科和关注点的参与。此处,关注点也脱离了社会需要,变成了去中心化、对灾难的需要。艺术体验是一种必要的外行体验,它证实了断裂或不可恢复的碎片的必要性,也证实了重塑统一与平衡之不可能性。作品变得必不可少,相对于形而上的本体论,试图复原碎片的政治、精神分析和科学意识形态的体系里,艺术体验具体地重建了断裂和失衡。
只有艺术是形而上的,因为它成功地将意义从外界转移到自身内部,它有可能将作品的一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而使其不唤起除自身外在以外的任何价值。
基本上,艺术的力量之源在于自身内部,作为用以建构图像的能量储蓄。而图像自身是个人意象的延伸,通过作品的强度上升到一种客观的、可确定的层面。没有强度,就没有艺术。强度指的是作品自我呈现的能力,也就是雅克·拉康所谓“凝视的驯化者”(gaze-tamer),在作品激烈的场域内惊艳、吸引观众的能力,在艺术循环、自足的空间内,它根据由艺术家造物主般优雅地创造、排除所有外在动机的内在形而上学法则运行。
作品本身就是艺术的规则与动机,这是它自身外在的实质。作品由材料、形状、在画作与符号中直接体现的思想组成,若不借助视觉,这些思想就无法被传达。
就这样,1970年代的许多作品中出现了被蓄意粉碎的意象,每一件作品内部都具有自身的强烈存在感,由一种受限于作品奇特性的冲动制约。因此,灾难的概念被确立,即1960年代受到语言认同原则影响的文化背景下不连贯性的产物。艺术界广泛的国际主义乌托邦形成了意大利贫穷艺术运动的主要特征,它一心超越国界,因而疏远、失去了最深刻的文化与人类学根源。
与意大利贫穷艺术运动中显著的游牧主义和1960年代的其他艺术经历相反,基于对方法论、技术相似性的认可,1970年代的艺术家们以一种多元化、且激励多元化的游牧主义回应1960年代,在一件件作品中发挥他们的敏感与转向。
大量意外出现的个人意象占据了艺术创造的主流。在此前的1960年代,去个人化、同质化、以政治至上的名义鼓吹去个人化的政治局势共同压抑艺术创造。现在正相反,艺术试图寻回艺术家的主体性,通过语言的内在结构表达自我。个体性获得一种人类学上的价值,因为它使个体即艺术家对自己的情感有了更新的认识。
作品变成一种微观世界,认可并赋予艺术充足的能力,以收复失地、重回拥有者的地位,认可个体性的流动,使其进入私人领域,将作品的所有价值与动机都建立在自身的冲动之上。
意大利语中“贫穷主义”(poversimo)的意识形态和观念艺术的无谓重复最终被超越,一种新的态度取而代之。这种观点认为,艺术作品内部的东西,作品展示自我、从自身内部获得的愉悦感、以及画作内容不受意识形态和学术忧思干预的自由,比其他所有东西都更重要。艺术在这种新的活动中重新寻回惊喜,拥有无限创造力,接纳自身冲动的愉悦,拥有万千种可能性,从具体形象到抽象图形,从天才的闪光到精细的媒介材质,这些可能性都互相融合,被作为有序而悬置的愿景,短暂地在作品的瞬时性上留下印记。
在游动的创造力中,1970年代艺术找到了自己的运动,也就是在各个领域内不受限制地、向各个流派借鉴吸收的可能性。艺术家马可·巴格诺利(Marco Bagnoli)、桑德罗·基亚(Sandro Chia)、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恩佐·库奇(Enzo Cucchi)、 尼古拉·德·玛利亚(Nicola De Maria)、米莫·帕拉迪诺(Mimmo Paladino)、雷莫·萨尔瓦多里(Remo Salvadori)在“超前卫艺术”这一变动着的领域内工作,意味着前卫主义各种实验性观念相互交织,假定每一件作品都包含了一种实验性的手作。艺术家对作品不再有预设,而是艺术家的手在艺术的实质中捕捉到一种介于思想与感知之间的个人意象,并推动其在自己的眼前成形。
艺术即灾难,是一场未经谋划而使每一件作品变得与众不同的意外。这种观念即使在前卫艺术及其传统的界限内,也为年轻的艺术家创造了一种可移动性。艺术观念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由不断运动变迁的回归、预想组成,它们永远不会重复,因为它们的路径以椭圆与螺旋式蜿蜒。
“超前卫艺术”意味着采取一种流浪的姿态,不在意任何定式的参与,心理情感、材料温度需与作品的瞬时性同步,除此之外,再无奉为圭皋的真理。
“超前卫艺术”意味着接受西方文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胜利,接受主张让步于作品直觉的实用主义。这种观念并非一种前科学的态度,而是一种成熟的后科学立场,它超越了从当代艺术到现代科学的拜物教式转变:作品成为一个精力充沛的时刻,从中获取力量加速,并在自身内部实现惯性。
因此,问题与答案在图像面前打成平手,艺术绕过前卫艺术的追问性,无视观者的期望,他们总是试图找到引发问题的社会学原因。而前卫艺术总是试图激发公众内心的不适而非愉悦,观众必须跳出作品,才能理解其完整的价值所在。
我将1970年代的艺术家们称为“超前卫艺术”主义者,通过呈现一个既是谜题又是答案的图像,他们探索着阐明作品含义的可能性。这样,艺术失去了它不为人知、问题重重的一面,也就是纯粹的探询,转向一种视觉上的明晰,意味着创作出佳作的可能性。这里,作品实际充当“凝视的驯化者的角色,也就是说,作品驯化了观者不安的目光,他们习惯了前卫艺术的开放性和预设的不完整,需要观众的干预使其到达完美。
1970年代的艺术倾向于将艺术变回一种令人满意的冥想,其中不管是神秘的距离或是遥远的遐想,都充满了由作品强度和内在形而上学生发的情色与能量。
“超前卫艺术”像风扇一样旋转,有一种敏感性,允许艺术向各方向运动,包括对过去的回溯。“查拉图斯特拉不想失去人类任何的过去,他想把一切都放在大熔炉中。”(弗里德里希·尼采)。这并不代表会错过任何,因为一切事物都触手可及,而不受过去或现在的任何世俗分类或层级制约。这是前卫艺术的典型特征,即以考古的方式重温过去的时光,并总是将其作为复活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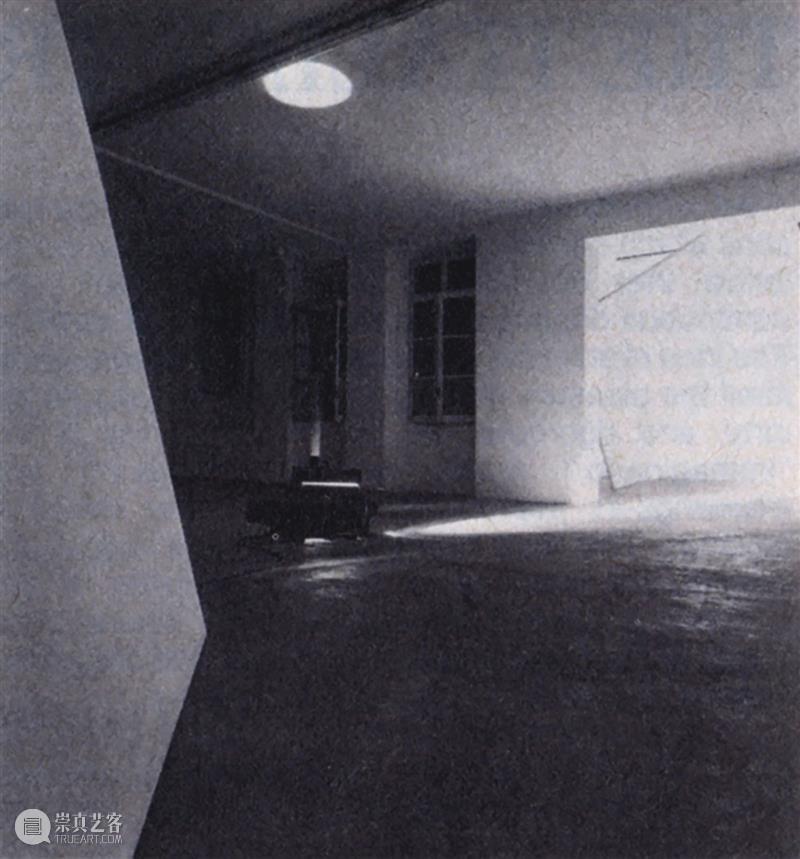
马可·巴格诺利(Marco Bagnoli),装置图摄于Salvatore Ala Gallery, 米兰 (1979) 图片来自于原文
马可·巴格诺利的作品是一项调查,在空间与时间的互动过程中、在空间与时间相乘的开放辩证法中,探询它们的实体价值和精神价值。这项分析关乎极限、空隙的概念,而差异与对立正是在极限、空隙中萌芽的。中心性的原则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歪斜灵活的关系。
通过绘画,桑德罗·基亚在一个想法的辅助下实践了这一手工性的理论,他在作品中注入一种形成于图形或标识独特性的假定。如果这个图像一方面揭示了想法,那么另一方面,它也是将其生产出来的图像化流程的证明,揭示了它的内在结构、反射的复杂范围、可能存在的对应、以及不同极性之间的移动和交叉引用。
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通过重复与转变进行创作。他从一个既存图像出发,通过绘画重现。然而,每次的重现都会改变和取代原本被复制的东西,其变化细微而不可预测。作品基于一种可预知的确定性,同时暗含了对初始规则的偏离。这一转变表现为歪斜的线条,也就是差异创作的一个显性特征。
恩佐·库奇接受了这一艺术运动,将他的个人语言隐藏在了“偏离”之中,创作中不存在停滞,而是形状、符号和色彩活跃地相互交织,渗入一种宇宙宏大视野之中。画作融入了多种元素的碰撞,并将其吸收成为画面微观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微观与宏观世界一起完成了交融,而混乱与秩序在燃烧中生成了沉淀和能量。
尼古拉·德·玛丽亚(Nicola De Maria)研究的是情感的渐变,通过绘画,作品既是精神状态的外化,又是在创作过程中产生的震动的内化。这样的结果就是建立了一个视觉的场域,形成众多点阵的交叉图景,在这一场域中,感受在空间上得以扩张,直到它们自身成为一种内在的结构。
米莫·帕拉迪诺的画作是揭示性的,也就是说,他倾向于将所有的感性,包括那些最内在的,全都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在视觉上。画作成为一个汇合与扩充之所,介于文化动机与感性之间。所有东西都被转化为画作、符号、物质的术语。绘画被不同的温度交织,热与冷、情感与思维、氤氲与稀疏,全部在色彩的量规下浮现。
雷莫·萨尔瓦多里的作品关注双重主题,将一个整体分裂呈现为两个相反的集合:雄性与雌性、前与后。将原本的身份与相似性分隔开来的隔膜线接近中间线,它产生了对称面,并将它们放在对立、不可调和的立场上。
当今,艺术创作意味着以一种循环、同步的方式将所有东西放在桌面上,个人图像、神秘图像、与文化史艺术史相关的个人标识,都被这种同步性在作品的内部混合。这种混合并不意味着对自我的神秘化,而是将自我同其他表达的可能性碰撞,从而接受将主体性置于所有事物交叉点的可能。“存在是许多人的谵妄。”(罗伯特·穆齐尔)。
作品被粉碎,也就意味着关于自我统一性的迷思被粉碎,在过去它指向个人意象永不止息的流浪,没有锚点,也没有参照点。这些全都加强了“超前卫艺术”的概念,因为它推翻了前卫艺术那种拥有至高无上参照点的态度。
每件作品都变化多端,跨越数个不同的参照系,利用每一件工具,它是受到色彩和其他媒介引导的手作,也是透过图像直击视野深处的思想家,像温度一样,使作品的碎片之间保持一种稳定而不统一的灵活关系。
不存在任何谵妄的规则,只有艺术的创意实践。它将所有不稳定因素维持在一种稳定的状态,而不将其转化为稳定和表面上的固定性。作品保留了其创作过程中在主体性边缘的活跃性痕迹,这种主体性不会变得出色,但会保留一个事件、一个领域之开端的特征。这不是前卫艺术对无限性的浪漫陶醉,而是在精神与感官的愉悦中漫无中心地漂流。
来自Flash Art n°92-93(1979)
意大利原文由迈克尔 穆尔( Michael Moore)翻译为英语
阿基莱·伯尼托·奥利瓦(Achille Bonito Oliva) 是一位在罗马的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他在1969年到1993年为Flash Art写作。
原文链接:
https://flash---art.com/article/the-italian-trans-avantgarde/

AP Project(艺术家研究出版计划)致力于创建一个面向研究型艺术家或艺术项目,进行文献出版、视觉展陈及作品收藏的平台,内容涵盖当代艺术家的研究与艺术实践,展陈研究与设计,艺术史中的出版物、艺术家写作、杂志、报刊、艺术家书籍。我们希望可以通过邀请艺术家进行创作,以不局限于出版物本身的展陈方式,通过实践,为推动研究视觉文化语言的研究。
同时“Artist Publishing Project”(AP Project)在意大利注册出版品牌,继续推进研究型项目。
翻译:韦淇
校对:黄文珑 祝天怡
微信编辑:朱思宇
正在展出:
欢迎订阅 YouTube 线上讲座回放
Subscribe to Our Online Talks Repl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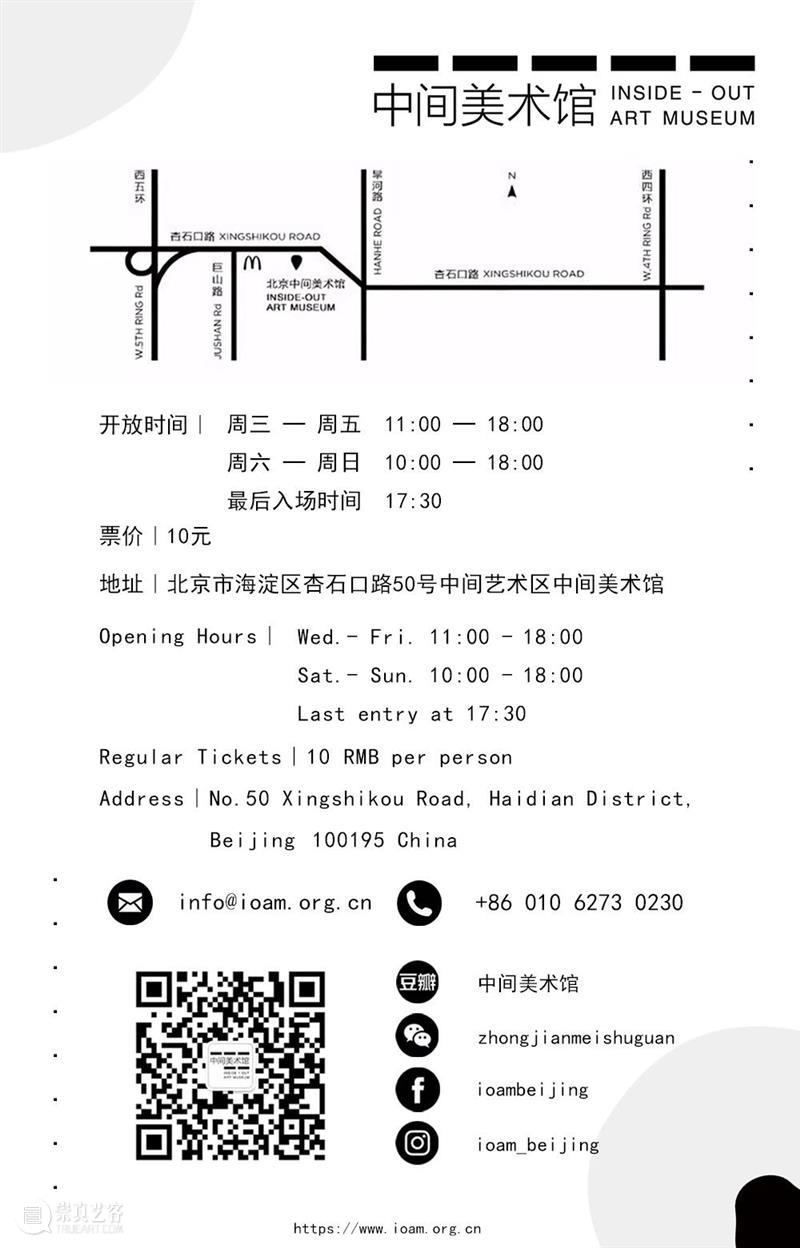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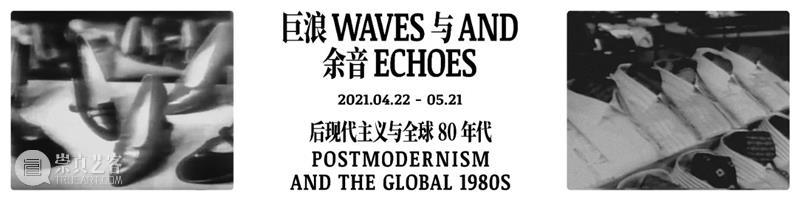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