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夫-阿兰·博瓦(Yve-Alain Bois,1952-)
《作为模型的绘画》导论:抵制要挟
简短回顾我们早先与哈克的对话,便会引出另一种类型的要挟,社会政治的(sociopolitical)要挟(为一件艺术作品提供一种社会政治阐释的职责,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讲,近来这项职责又有了新的补充,那就是让他的作品具有明确清晰的社会政治意义)。在我们1977年关于格林伯格的争论中,政治问题,是条鸿沟,是条分界线:假如你是一位形式主义者,你就是一个保守的反动派。让·克雷伊和我,经历过1968年5月风暴的人,都觉得这种种怨恨的激烈是相当莫名其妙的:我们从来不希望自己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当我看到,在今天的美国,对艺术提出的要求要比别处更胜一筹时,我也会感到同样的震惊。(在这个国家里,政治的意义看起来是极其微不足道的——见证了上次总统选举的乏味,以及研究生普遍缺乏政治意识的状况——然而也许在这儿,这些要求是最强烈的。拿日本和美国作对比,罗兰·巴特曾写道:“在日本……性感只存在于性活动中,并非到处都是;在美国,情况却正好相反;性活动无处不在,只是在性感中没有。”[15]我想说,在美国,政治活动泛滥于各处,恰恰在政治中没有。)但是这些对立的术语却并不怎么新鲜:众所周知,现在被称为“苏联前卫运动”(“Soviet avant-garde”)的非凡艺术冒险,因为一种相同的社会政治要挟的规定,而被唐突地掐断了命运。不仅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还包括一连串的艺术家、电影导演、作家、建筑师等,也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以他们的“形式主义”为由而噤若寒蝉。尽管,梅德维杰夫/巴赫金恰当地承认,在一般情况下,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争在俄国“本质上缺乏成果”(第67页),但这场争论一方的介入,在我看来,从没有这么真实可信过。1932年,当斯大林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俄国发生的文化事件时,为了通力办好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庆典活动,《电影》(Kino)杂志公布了这条标语:“我们的电影必须走向意识形态的丰富!”爱森斯坦极富勇气地在这本杂志的下一期里断然拒绝了这项指令。他首先查阅了字典(“我对字典有着疯狂的喜爱,就像一种病态”),他发现“意识形态”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的理念(idea)这个词,继而被快速投入到他的希腊语/俄语字典中:“理念,爱奥尼亚词汇。(1)外貌,外在外观;(2)图像,类型,方式,属性,特质……;尤其是:表达方式,话语的形式与类型;(3)理念,原型,典范。”
因而:有必要再次想起理念在起源上的不可分离性(inseparability)(第3点),表达方式上的不可分离性(第2点),以及……外貌,外观的不可分离性(第1点)。
这新颖吗?就像波波夫的名字一样新,过去经常被用来书写这样的“发现”的Sacha Tchierny。然而,假如它并不新颖,那么它就是那些人们必须反复不断地在午餐和晚餐之前向自己重复论述的真理之一。对于那些在睡前不进餐的人,也是如此。但是,对于大多数完全清醒的人而言却并非如此,因为这种人必须在他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它。[16]
爱森斯坦的论述,非常符合梅德维杰夫/巴赫金眼中“欧洲形式主义”的主要诉求,即“形式总是意识形态的”,[17]而《电影》的口号却假定任何形式可以在意识形态上是“空无的”,被剥夺了内容,这种口号要么是完全幼稚的,要么就是完全不诚实的——这取决于“形式”被考虑和顾及的水平。在定义介绍之后,他摆出的第一个姿态,便是指责“形式主义”这个标签:“当一位电影导演开始思考关于将一个理念物质化具体化的手段问题时,很快,对于形式主义的怀疑或指控就会复仇似地落在他的身上……为了给这样的导演洗礼,‘形式主义者’分享了同样草率怠惰的鼠目寸光,就像所谓的科学家将梅毒的表征解释为‘感染梅毒’的Klux一样。”[18]但是,爱森斯坦的智慧不止于此,为了再次重申他对形式问题的承诺(这篇文章题为《为了形式的利益》[“In the Interest of Form”]),他采用了一条非常狡猾的策略,一条解除他的敌人的武器的策略。假如,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形式”被描述为一种讨厌的东西,那么,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他将把“形式”从他所谓的一种意识形态的“3K党(Ku Klux Klan)”的支配下解救出来:
这恰恰是对形式的错误欣赏,在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写给梅林(Mehring)的信中,他提到,形式曾被忘记:
“我仅仅想要提醒你注意这个现实,马克思和我都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我们对它的审视在我们的作品中是完全不够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同样都心怀愧疚。坦率地讲:我们把一切都放在引力的中心,而且在当时我们必须这么做,并且依据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普遍识形表征,以及由它们所决定的行为,我们必然如此推论,而位于这些表征的根基的,是经济因素。在这情况下,因为内容,我们就没有关心形式这个方面,而它本该被考虑:那此表征是以何种形式构成呈现的,等等……这是老生常谈了:首先,因为内容,一个人从不关注形式……但我想为你指出这点,从今往后提醒你注意它。”[19]

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1898-1948)
这确实是“老生常谈”,而且,尽管恩格斯的“构想”仍然预设了注意力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分离的可能性,但对于曾阐述过这种分离之不可能的爱森斯坦来说,这个段落已被证明是一枚针对他的强力炮弹。为了以另一种方式描述这种不可分离性(inseparability),我想再一次求助于罗兰·巴特。为了回应关于他的形式主义中非历史性特征的数以千次的疑问,巴特辩论说:
一个人总是不间断地听到它不厌其烦地强调,形式主义天生就与历史格格不入,这种现象可真显著啊。我自己却总是尽力去表明形式的历史责任(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感谢语言学和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我们才可能最终避免社会学和历史通常将我们带至的死路:将历史不恰当地缩减为历史指示物的历史(history of referents)。其实,存在一个形式、结构、写作的历史,这个历史拥有它自己的特殊时刻——更确切地说,多个时刻:恰恰是这种屡次出现的特殊时刻,威胁了一些人。[20]
巴特在这儿顺带提及的问题,曾是俄国形式主义在其末期的本质问题,尽管梅德维杰夫/巴赫金在对待这个问题时,宁可不正直地忽略这个理念,以期以相同方式重构它自己。[21]无疑是为了反击“马克思主义的”反形式主义运动,朱里耶·蒂尼亚诺夫(Jurij Tynjanov)的卓越论文《文艺进化的问题》(“The Problem of Literary Evolution”,1927)和蒂尼亚诺夫、雅各布森随后合写的《文学和语言研究中的问题》(“Problem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28),都是对早期什克洛夫斯基捍卫艺术作品绝对自主性的批评,正如刚刚提到的巴特的话一样,是对历史研究与结构研究之间相容性(compatibility)——甚至相互支持——的肯定。[22]通过拒绝粗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艺术作品看作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的观点,作者强调,在经济基础(下部构造)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人工产品)之间的关系,不应被分析得过于快速直接,也不能被直接地观察。他们认为,这种鲁莽武断,总会走向一种艺术观念,即把艺术仅仅看作是一个社会政治构造的图解和一种现实投射而已;而艺术的特殊性却被牺牲在超验能指的祭台上。为了避免这种反映论的陷阱,比如,在俄国,它便最终导向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导向了对那些不赞成这个观点的每位艺术家或作家的有组织谋杀,因为这些艺术家和作家主张,一个人必须首先描绘一幅图画,一幅呈现任何历史时刻的上层建筑中每个扇区(sector)间相互关系的整体图表。只有在这些关系——比如那些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被清楚绘制之后,一个人才能开始尽力分析,整体图表(系列的系列,系统的系统),以及这个整体图表所绘制的与同时代社会相关的特殊领域。但是,因为这些不同文化系列(艺术、宗教、哲学等)往往以不同的节奏发展着,在他们的论述中,这点可是个决定点(decisive point),每个历史横剖面或历史地图都会承受一种具体特有的特征,经考虑分析,就是具有认识论性的时代图画——福柯后来会称其为一个给定时代的秩序性图表(tableau)和认识性图像(épistémé)。这种对各种“意识形态”系列间结构关系的历史特殊性的强调,正是巴特在说到“形式的历史责任”(“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of forms”)时他心中所持的观点;而这也正是导致他将激进话语全盘否定并控诉其无关历史的原因。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我能同时忠实于巴特的教导和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警告。在接下来的篇章里,读者不会读到对于任何作品的任何直接的社会政治分析,因为假如艺术确实可以实现一种政治要求,那么这种政治要求只能是它自有的层面,即,一种意识形态层面,它自已的分层(itself stratified)。这丝毫不意味着,最终社会政治没有渗透进分析之中。如同“西方形而上学”或“先天投射”(“a prior projection”)这些概念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会常常出现,每一次都指出,被讨论的作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抗着它们所具体体现的东西。更率直地说,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表现了对唯心主义的强劲攻击。没人会否认,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对立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我的观点是,假如一个人不想把艺术和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限定于仅仅一个主题问题(这样接下来就会出现一种“政治”和“非政治”艺术之间的无用二分法),那么,他必须要做的,就是净化提炼(refine)意识形态分析(确实,那些被称为“政治艺术”的绝佳范例总是存在于一种主导意识形态的代码和策略的破译中——这种情况今胜于昔)。这便隐含了一种对于“结构或形式的历史”的极其特别的关注,因为“形式往往是意识形态的”。
我们不该太快地扔掉形式主义这个词,因为它的敌人们是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宇宙因果论者,唯心论者,实用主义者,“自发主义者”(spontaneists);攻击形式主义的名义,往往是内容、主题和动机(Cause,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模糊词汇,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一种信念和一种决定论,好似它们是同样的事物);也就是说,是以所指(signified)的名义,以名称(Name)的名义。我们不需要与形式主义保持距离,仅仅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舒服安逸(ease/舒适与欲望同类,远比与责难同属的疏远/distance要更具有颠覆性)。我心目中的形式主义,并不取决于、在于“遗忘”、“忽略”和“缩减”内容(“人”),而在于这样的品质,即它在内容(让我暂时保留这个词)的门槛之前并不停止前进;内容恰恰是让形式主义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它无尽的任务,便是每一次都要把内容推回原处(直到原点概念不再切题相关),还要按照连续形式(successive forms)的操作来替换内容。[23]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
这最后一条引用,击中了最后一种类型的要挟,这种类型的要挟压缩了除理论要挟之外的所有前述要挟类型,并且彻底控制了整个艺术史领域,并在20世纪艺术史这个子领域中显示了独有的力量。让我最后一次从巴特那里借用一个概念,我姑且称其为失示意能症(asymbolia)。它是一种病理性疾病,会影响人类感知和接受共存性意义(coexisting meanings)的能力,失示意能症是一种符号示意功能萎缩症。[24]但是,这种疾病又极难诊断,因为,与大声声援它的受害者比起来,没有人会更大声地疾呼它的内容,没有人会更多地表达出对于“回归内容”的需要。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继续理解这个医学上的隐喻:反形式主义批评家拒绝将形式看作别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病毒,正如反形式主义者一样,失示意能力的批评家将意义构想成一个组成部分,而它在某一时刻是缺席的。他从没有如他证明某物“拥有”一个意义时那样高兴。但是,谁又曾认为,例如蒙德里安或马列维奇或罗斯科的艺术,是毫无意义的呢?当然,许多人和失示意能症的受害者一样,他们对于一件艺术品的意义和指示物(referent)之间的区分存在困惑,或者,用巴内特·纽曼借用的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的话,他们对于“主题”(subject-matter)和“客体”(object-matter)之间的区分存在困惑,正是这种困惑使他们共享了一个建立在这种困惑上的基本原则。抽象艺术的反形式主义敌人们坚持认为后期抽象艺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艺术在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里没有显在的指示物,依循同样的逻辑,患上失志意能症的批评家最终承认这种抽象艺术进入他的美学神殿,因为他有能力精确地找到这一类指示物了。只有当他已经揭露出这个指示物,并宣布它是这幅被讨论的作品的唯一可能的含义(signification)时,他才能安息。就像巴尔扎克小说里那些观看画家弗兰霍菲(Frenhofer)“无名的杰作”时目瞪口呆的目睹者一样,他,也已经发现了“隐藏在底面的女人”,既然如此,他就感觉到,他的任务结束了。要给这样一种失示意能症举出大量例子,可不会是件难事。如果说,在20世纪艺术研究的子领域里,这种失示意能批评的吸引力更为强大(因此,我坚持认为,抵抗这样一种压力是必要的),那么也许,这是因为符号的指称性(referentiality)恰恰是模仿性再现(mimetic representation)的主要理念,而这个模仿论,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艺术所想去质疑的理念。但更为明显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艺术史作为一个学科,尤其在美国,已经深深地中了它的魔法,难以自拔。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我想,是这个国家艺术史学科中图像学模型(iconological model)的势力,这让我想到了潘诺夫斯基(Panofsky)。潘诺夫斯基首次创造使用图像学(iconology)这个术语的著名论文至少出现在两个不同版本:1939年的《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中,和1955年的《视觉艺术的意义》(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中。(1939年的版本本身便是1932年一篇文章的修订版,而1932年的那篇文章的论点,在一本1930年出版的书里便首次提出了。)[25]尽管潘诺夫斯基在《视觉艺术的意义》的前言里从相反的方向进行了评论,但是他在1955年版本里的修正,却是极其重要的(这种修正是量和质的变化)。正如麦柯·霍利(Michael Holly)注意到的,潘诺夫斯基在1939年谈及的“(与狭窄意义相对的)更深层意义上的图像志(iconography)”,到了1955年变成了与图像志相对的“图像学”。[26]我把这种从“图像志”到“图像学”的滑移,解释为一种拒绝(disavowal)的策略,一个意欲掩饰事实的面具,这个事实是,在实践中,图像学经常成为传统图像志研究的一个精密复杂的、绝顶聪明而精心发展的变体。潘诺夫斯基意识到了这个事实(所以戴上这个面具),他必然将这个事实解释成他对自己年轻时思想的自我背叛。就这一点而言,霍利所引用的潘诺夫斯基写给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的信中谈及《图像学研究》的段落,自然非常重要了:我努力要去解释清楚的事,真的并非完全原创。也许,只有在与那许多对艺术作品的纯粹形式主义的阐释进行对比的时候,图像志的工作成果才显得不点不同寻常。事实上,我的方法不是革命性的,而是保守的,而且,当一些批评家告诉我《一个医生的两难选择》(“Doctor’s Dilemma”)老医生告诉他的年轻朋友的话时,我一定毫不惊讶,这个老医生说:“你的发现其实在40年前就已经被发现了,你可以为此自豪,”以及类似此句的话。[27]
到了1966年,面具自己都觉得没有必要再掩饰了。在法文版《图像学研究》的卷首语里,潘诺夫斯基写道:“今天,也许我会把标题里的关键词图像学替换为图像志,这样读来会更熟悉,更少些争议;但是——承认这点让我充满了忧郁的骄傲——事实上,这一置换在今后是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恰恰是这种种版本的《图像学研究》存在的一个后果。”[28]当然,我们可以相信潘诺夫斯基说的是真话,把他发展出来的图像学方法贬低成“新瓶装旧酒”,可是,这样既不公平,也不愚笨无智。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在信中传达出的失望感,以及在1966年法文版前言里写道的“忧郁的骄傲”。实际上,在他早期的文字里——其中大部分仍未被翻译成英文——潘诺夫斯基试图这样去写作艺术史,即,将嵌入于艺术作品的各种形式体系,与一种从社会、心理学和意识形态方面来解释风格演变的方法连接起来。如果说,他能够在20年代便追求这些绝妙的研究途径,而这些途径所导向和带来的是他那些论述人体比例和透视的著名理论篇章,那是因为,他当时已经怀抱以下理念:在结构层面上,艺术形式在塑造一种“艺术意志”(Kunstwollen)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里所使用的李格尔的概念,他曾在一篇出色的论文中试图加以澄清。换言之,因为他不认为形式是一个补充。虽然潘诺夫斯基逐渐地抛弃了这个复杂概念,转而开始发展出一种直接得多的、层次不那么多的连接艺术史、观念史与社会史的方法。继而出现的,是一种简单得多的对主题的强调,而主题是在联系文本时才被理解的。最终,他早先所希望在艺术作品中确切说明、接合表述的整个复杂的意义结构——他对(1)“结构方案”(例如,透视)、(2)主题、(3)“世界观”和(4)社会史这几项之间的辩证联系的调查研究——最终减低为鉴定出一个主题的行为了,因为他认为主题是意义的唯一代理者(sole agent):每件艺术作品成了一个单维肤浅的画谜,一个隐蔽寓言的承载者,必须被适当地破译。因此,绝非偶然的是,正是由于在这个国家图像学成为统治性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学者们对意义的可能性的研究和对意义结构(实际上这个意义结构围绕着主题学,但只是作为主题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的研究,也越来越不投入了:我为我的著作所设定的其中一个目的,便是打断这种状态。再一次申明,对20世纪艺术进行图像学研究,我不持任何异议,因为我考虑到,它更为有限的意义概念,并没有阻止分析深入到其他的解释层面,和其他的意义层次(strata of signification)。举例来讲,听闻到毕加索赋予吉他的形象以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意义(不仅如此,还是女性化的),对于这样的观点,我是非常乐于接纳的;但我憎恶任何人断言毕加索的吉他的意义是“女人”。一方面“女人”就其本身而论并不是一个意义,而是一个指称(referent),它可以关联到一个巨大的意义数组(a vast array of meaning);另一方面,我更感兴趣的,是对毕加索立体主义作品中符号的符号学波动(semiological fluctuation)的结构性可能进行研究。
潘诺夫斯基(wolfgangk. h. panofsky,1919—2007)
最后但同样重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潘诺夫斯基对于直接以图像学方法进入现代艺术、尤其是抽象艺术的狂热,发出了警告,抽象艺术是本书后面的论文中着重论述的艺术类型,实际上也是我的研究的主要部分。让我们回到我先前对“图像志和图像学”两个版本的文献学(philological)比照吧。在上文讨论过的那个包含术语置换的段落里,潘诺夫斯基所在进行的,是把对他的著名的三层理论的说明,与这个理论列出的三个解释层级的层次嵌套(hierarchical nesting)进行交换(主题的确认是解释图像历史或寓言意义的准备,它本身也是它的“内在内容”解释的准备)。然而,这个说明性的片段,以一个限制(restriction)告终,看来这句话并未受到潘诺夫斯基的信徒的注意:解释层次的层级结构是必要的,他在1939年版本的论文中写道,
除非我们处理的是这样的作品,即在作品中,整个次要或传统主题的领域都被消除了,主题(motifs)到内容(content)的直接转换却是它要尽力达到的,欧洲风景画、静物画和风俗画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伴随标示着后来者的异常现象,从整体上讲,我们所处理的,即为经过漫长发展后的过度复杂阶段。[29]
正如伯纳德·忒西德(Bernard Teyssèdre)在这篇论文的法文版本里所观察到的,在1955年的版本里,潘诺夫斯基的文句遭遇了三个修正:(1)最后一个分句(即“大体上,除了后面要标记的异常现象”这句)被删除了;(2)贬义词“谋求”被“达到”(is effected)所代替;(3)对于“欧洲风景画、静物画和风俗画”这个列例,潘诺夫斯基在后面附言“更不必说‘非具象’艺术”[30]。这第三种变形,在这里明显是我关注的,尽管我应该指出,他虽然删去了他对于风景画、静物画和风俗画所暗含的负面价值判断,却一点都不意味着潘诺夫斯基已经最终撤销了他对自已方法的普世性的宣称,也不意味着他正把他的方法限制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传统作品上,也就是那些题材来自于文本的艺术作品。[31]但是对于抽象艺术的论述却是一个警告:对于图像学方法研究抽象艺术,他深感沮丧。这个警告,无疑来自于他自己对这个现象的困惑(正如纽曼有点夸张的表述一样,我们不应对那“始终展现出他自己对丢勒以来任何艺术作品都毫无感觉的人”期待太多)[32],但是至少,潘诺夫斯基不敢在文章中说:假如他的方法行不通,那就是研究对象的错。重要之处在于,图像学的创立者自己都声称,它不是研究抽象艺术的最佳工具。就这一点来说,他完全正确。也许潘诺夫斯基愈来愈严重的失示意能症,是他移民到美国的一个后果。尽管他不是一个流亡者(大多数德国艺术史家以这样的身份移居到美国和伦敦),潘诺夫斯基却和那些不如他幸运的同事们一样,具有一种想要完美融入新国度文化组织的强迫症。在《美国的艺术史研究三十年》(“Three Decades of Art History in United States”)这篇标题有些不确切的“移民”文章里,他提供了一个线索。他首先提到了被投进一个全新的学术氛围所带来的自由解脱效应,在当时,这个全新的学术环境对标志着欧洲学术研究的那种偏狭和民族主义的偏见也一无所知,让他感到大为吃惊的,还有他被迫忍耐的语言上的和认识论上的突变。即使他捎带提及了与他发现的传统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潘诺夫斯基还是把欧洲学者抵达美国、遭遇“原则上不信任抽象思辨的盎格鲁-撒克逊实证主义”这个事实,看作是一个“恩典(blessing)”。[33]对于潘诺夫斯基来讲,快速掌握英语,便是急需完成从而掌握工具的重要任务。“不得不以可被理解的方式、准确地、清晰生动地表达我们自己,让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但完全是可以做到的,”这位德国移民故意经受了一次猛烈的切除手术:
不幸的是,德语竟然允许从一个由很深奥的含义织成的帘幕后面来猜测非常烦琐的思想,反之,也允许在一个术语后面埋伏下大量的含义。比如,taktisch(策略的,战术的)这个词,一般说来是指与“战略的”这个词相对的“战术的”这个词,而在德语的艺术史中,它就成了“tactile”(具有浑厚坚实质感的)这个词的同义语,甚至成了“textural”(肌理的)这个词以及“tangible”(有实质的,有形的)和“palpable”(摸得出的、容易感觉到的)这些词的同义语。到处出现的malerisch(绘画的、可以入画的)这个词,则可以按照上下文的意思翻译成七八种不同的含义:在“picturesque disorder”(如画般错落)中就有“picturesque”(如画的)含义,还有与“plastic”(造型的)相对的“pictorial”(绘画的)含义,(更令人吃惊的是还有“painterly——画家的”这种含义),或者还有与“linear”或“clearly defined”(强调线条的或明确限定的)相对的“dissolved”(溶散的、渐隐的)“sfumato”(以渐隐法,以烟雾画法)或“non-linear”(非线性的,不强调线条的)这些含义,以及与“tight”(紧凑)相对的“loose”(松散)这种含义,还有与“smooth”(平滑)相对的“impasto”(厚涂)这种含义。总之,在讲英语或用英语写文章时,即使是一个艺术史家也要多少知道他在说什么,也要说话算数,而这种强制对我们大家都有莫大的益处。[34]
潘诺夫斯基拿自己在美国的初次登台自嘲,很快,这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就把读者赢到了他自己这边。(谁能像他一样,不和李格尔“艺术意志”[Kunstwollen]的不同含义斗争呢?)但是,这种自身强加的讽刺实际上掩盖了一种糟糕的哀痛感:虽然他在美国写的文字可以被解读成一种对他年轻时反实证主义姿态的驳斥(他奋力达成“先验科学的”艺术史征程的“失败”,促成了这种对年轻时立场的反驳),但他信奉的语言经济观——1词1义——最终拒绝承认语言拥有自己的生命,语言符号所具有的涵义对解释无限开放,这种观念将塑造他的图像学所采纳的、缩小了的意义概念。因为,假如以明晰的名义,在malerisch这个词的七、八个可能的含义中,只能有一个被保留下来,这就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种损失——正如把毕加索《吉他》的寓意解读为一个女人,但是假如只有这一种可能的含义,我觉得,那就是一次可怕的减少了,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与这种还原减缩论斗争。声称任何一个词、一件艺术作品只能具有一个意义,和声称它们真的会纯粹地缺失意义,这两者之间只有一种程度上的差异,而非本质上的区别,实际上,一个主张常常来自于另一个(假如不是这个意义,那么它肯定什么都不是)。这两种空想,都预示一个冻结的符号世界(好像意义在历史上没有变化,好像旧符号没有出现新意义),这两者都是失示意能症的症状,它们打断了解释链,盖上了潘多拉的盒子,而当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去打开它。理论主义,反理论,时尚,反形式主义,社会政治要求,失示意能症:这些,都是我工作领域内正活跃着的势力,各种各样的路线绘制了我所从属的领土地图。至少,它们是我能够认识到的势力,也是我认为的最致命的势力,在接下来的文章里,我把他们当作为批判的靶子,尽管常常是含沙射影的含蓄批评。这并不意味着我总是成功地远离这些力量。这同样也不意味着,许多其他未被发现的势力,或者,那些我没足够准确地感知到它们紧迫的破坏力的势力,并没有在我所讨论的领域里投下它们的阴影,实际上,虽然我没有意识到它们,但它们也要影响我的论述。对于最后谈到的这些,我明显无法提供解药;它们是我的盲点,是我的视野里未看见的部分。然而,我着实希望,在我对这个领域的理解里,足够多的问题能够被拎出水面,从而让我的书具有统一的针对性,也让接下来的文章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讲授抵抗力(resistance)的一课。
本文译自Yve-Alain Bois, Painting as Model,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90.中译本《作为模型的绘画》,诸葛沂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0年出版。
[美] 伊夫-阿兰•博瓦/著
诸葛沂/译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20年

注释:
[15]Roland Barthes, Empire of Signs(1970), English tr. Richard Howard (New York:Hill and Wang, 1982), pp.28-29.[16]Sergei M. Eisenstein, “In the Interest of Form”(1932), French tr. Luda and Jean Schnitzer, in Au-delà des étoiles, ed. Jacques Aumont(Paris:UGE, 1974), p.234.[17]Ibid., p.239. 接着在爱森斯坦的文本中,写道:“形式首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不能租借的。自然并没有准备好,把意识形态中心分配到合法的所有者身上。”(pp.240-241)。[20]Roland Barthes, “On The Fashion System and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1967),interview with Raymond Bellour, English tr. Linda Coverdale, rpt. In The Grain of the Voice(New York:Hill and Wang, 1985), pp. 50-51.[21]参The Formal Method, pp.14-15, 23, and 26-27.[22]这两篇文章都刊于英文版的Matejka and Pomorska, 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 pp.66-78 and 79-81.[23]Roland Barthes, “Digressions”(1971), interview with Guy Scarpetta, English tr. In The Grain of the Voice, p.115.巴特使用的“scientiste”这个词,不应该被翻译成“科学家”——巴特一点都不对抗科学——尽管我不知道与此同义的英语词语(“科学学者”?)。一个“scientiste”,在法语里,意味着一个人敬畏科学的密码和符号,要胜过于科学本身。像这样,“Scientisme”,就与假科学有着很大的关系(例如,“第四维”的红鲱鱼便是一个典型的“科学”神话)。[24]参Roland Barthes, Criticism and Truth, tr. Katrine Pilcher Keuneman(London:Athlone Press, 1987), pp.52 ff. 实际上,这个词明显是巴特从以下书中借用的:H.Hécaen and R.Angelergues, Pathologie du langage(Paris:Larousse,1965), p.32.[25]参Michael Ann Holly, Panofsk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rt History(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59. 1932年的文章取名为“Zum Problem der Beschreibung und Inhaltsdeutung von Werken der bildenden Kunst”(《论艺术的描绘问题及其内容阐释问题》)。它反复逐字逐句地引用著作《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 at the Crossroads)中的段落,后者在1930年由瓦尔堡学院出版。当前这个致力于去描述潘诺夫斯基的段落,来自于我撰写的关于霍利(Holly)的书的书评(“Panofsky Early and Late,”Art in America, July 1985, pp.9-15.)[26]参 Holly, Panofsky, p.233, note 6. 1955的版本题为“图像学与国像志:文艺复兴艺术研究导论”,相关段落,见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p.31.[27]引用自Holly, Panofsky, 9.169.[28]Erwin Panofsky, 法语版《图像学研究》的前言(Etudes d’iconologie, trl Claude Herbette and Bernard Teyssèdre[Paris:Gallimard, 1967], p.3),从法语再译过来,在这里我要感谢赫伯特·凯斯勒(Hrebert Kessler)提醒我注意,潘诺夫斯基最后对于图像学/图像志二元对立这一观点的放弃。[29]Erwin Panofsky, “Introduction”, Studies in Iconology: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8.[30]参Cf. Etudes d’iconologie, tr. Herbette and Teyssèdre, p.23, note 1.[31]直到斯维特拉娜·阿尔帕斯(Svetlana Alpers)《描绘的艺术:十七世纪的荷兰艺术》(The Art of Describing: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一书的出版,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才有能力处理甚至面对非寓言式的荷兰艺术的特殊性。实际上,正如阿尔帕斯对潘诺夫斯基一篇脍炙人口的论文《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这一标题所作的评论中所指出的,潘诺夫斯基的整个计划是“建立在对于人与艺术的文艺复兴假设之上的”(“Is Art History?,”Daedalus, Summer 1977, p.6.)毫不奇怪的是,除了1924年出版在慕尼黑出版的Die deutsche Plastik des elftenbisdreizehntenJahrhunderts(仍没有英译本)以及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New York:Meridian Books ,1957)之外,他所写的关于中世纪艺术的所有文字,都充满了私人性的或消极的言外之意。甚至像《文艺复兴与西方艺术中的再生》(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in Western Art, Stockholm, 1960),关注的几乎完全是前文艺复兴时期,照样充满了私人性的或消极的言外之意。对于这点,参Jean Molino,“Allégorisme et iconologie:Sur la méthode de Panofsky,” in Erwin Panofsky, coll.Cahiers pour un temps(Paris:Centre Georges Pompidou, 1983), pp.27-47, 以及Jean-Claude Bonne, “Fond, surfaces, support(Panofsky et l’art roman),” ibid., pp.117-133.[32]Barnett Newman, “Letter to the editor,” Art News, September 1961, p.6.[33]Erwin Panofsky, “Three Decades of Art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1955; rp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329.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与其内容更为近似,即《一位欧洲移民的印象》(“Impressions of a Transplanted European”)。这篇文章最早于1953年出版,标题很简单,即《艺术史》,在一本取名为《文化迁移:欧洲学者在美国》(The Cultural Migration:The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中的一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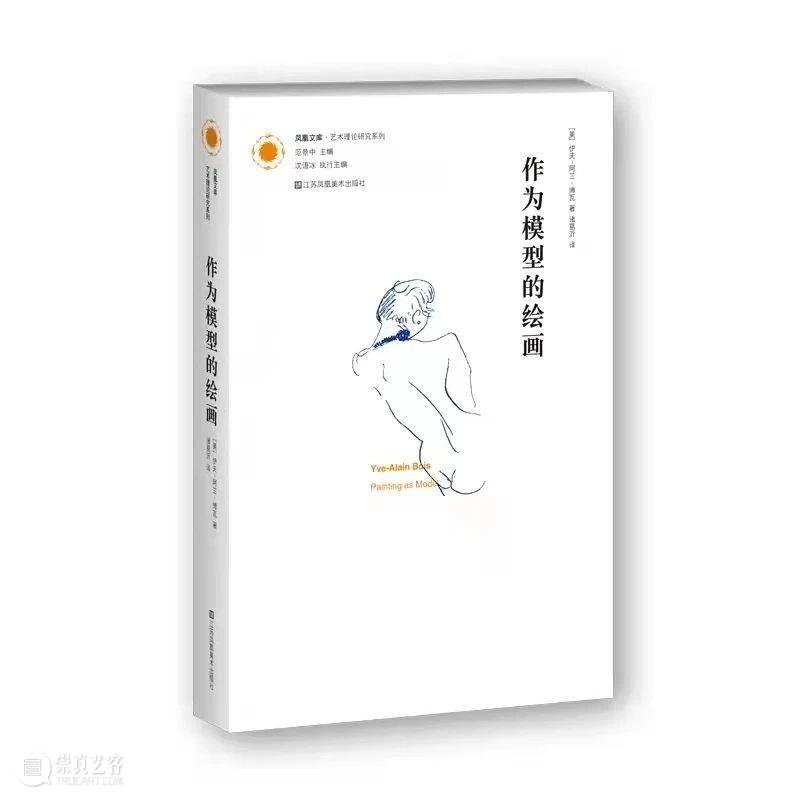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