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疫情席卷全球,弗朗西斯·埃利斯在社交媒体上所透露的行踪回归寂静,让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不会在今年十月底于香港大馆当代美术馆开幕的个展“水限__陆界:边境与游戏”中现身。然而,在一个宁静小岛上度过14天隔离期后,埃利斯依然充满惊喜地出现在香港观众的视野中。距离上次人们在东亚看到他的身影已经过去整整两年,2018年他曾屡次前往上海与首尔,呈现他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首次中国个展“消耗”、在首尔Art Sonje Center的首次韩国个展“弗朗西斯·埃利斯:直布罗陀航海日志”以及光州双年展。

展览开幕时,埃利斯与策展人谭雪、大馆艺术主管Tobias Berger进行了一场对谈,刚结束在香港取材拍摄的他似乎略显疲惫,但提起自己长途跋涉而来的经历,他仍然感到兴奋:“我希望能保持创作,将自己已持续数年的对话不断进行下去,在场——这是我来到香港的原因。”这符合我们对这位艺术家的了解,即时即地的现身以及充满魅力的参与:一如他在作品《龙卷风》(Tornado,2010)所展现出的那样,在短短42秒的影像中,他义无反顾地奔跑追随着变幻莫测的龙卷风路径,单薄的身影在庞大如巨兽的风暴中心若隐若现。即便是龙卷风也无法阻止他的创作,全球性爆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则使他的行动更具有现实意义。
弗朗西斯·埃利斯,《龙卷风》片段
视频来源:Francis Alÿs
与当下共处:在每个现场

弗朗西斯·埃利斯,《桥》(Bridge/Puente),2006年,影像静帧
 弗朗西斯·埃利斯,《水限__陆界:边境与游戏》
弗朗西斯·埃利斯,《水限__陆界:边境与游戏》2006年,弗朗西斯·埃利斯创作了《桥》(Bridge/Puente)。该项目始于美国1995年的“干湿脚”政策,“湿脚”即是于海上被拦截的古巴移民,他们会被遣送回古巴;若是“幸运”地在陆地被逮捕的“干脚”则能够居留于美国。2005年,一群古巴船民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群岛间的一座桥上被截获,这座桥究竟该归类于陆地还是水域?该事件陷入了法律的尴尬境地。以此为启示,埃利斯召集了来自两岸的150余艘船,船身相连以连接两片陆地。这个作品也成为此次大馆展览“水限__陆界:边境与游戏”的契机,它无形间与70年代香港政府的“抵垒”政策(在海上或新界被截停的内地移民会被遣返,而进入九龙与新界交界处以南的移民则可留下成为合法居民)产生了跨越地域与时间的共鸣。即便是在东亚,他的创作也在不同范畴中被不断引申出新的意义,与新的时空和语境发生反应。
在埃利斯早期的实践中,他曾携带一罐底部穿孔的绿漆行走在耶路撒冷的停战边界,用身体的移动画下“绿线”(《绿线The Green Line》,2004);或是在巴西圣保罗,提着一罐渗漏的颜料在画廊周围闲逛,最后沿着痕迹回到画廊,将空罐悬挂在展览空间内(《漏 The Leak》,2002)。对埃利斯而言,他关注的是某两者之间游动的张力,涵盖了地理上的“割据”,公民身份的“边界”,公共空间与私密性的“界限”乃至实践与结果的“悖谬”。这些理解与埃利斯的生活经历有关。1986年,任职建筑师的他移居墨西哥城。这个城市与香港相似,都有着复杂密集的人口流动与结构。外来者与当地人的身份形成一种暧昧模糊的碰撞,他遭逢了当地“如潮涌至的社会复杂性”,这促使他以“一种循序渐进的艺术实践去干预与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从而建立对话”,在他看来,“这是面对他所遭遇的城市环境相对高效的回应。”自90年代起,埃利斯就身体力行地游走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中,他曾在采访中提及,与其通过档案来还原对一个地区的认知,他更偏向于通过无数次“干预”来对现实的惯性提出质疑。

弗朗西斯·埃利斯,《绿线》(The Green Line),2004年,影像静帧


弗朗西斯·埃利斯,《漏》(The Leak),2002年,影像静帧
2020年无疑改写了许多过往的传统经验,现代人开始体验到一种从未想象过的生活。人们足不出户,旅行也成为奢望,一次次疫情的宽松与紧缩模糊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似乎验证了他最耳熟能详的“推冰”作品《实践的悖论 1(有时行动只能引向虚无)》(Paradox of Praxis 1: Sometimes Making Something Leads to Nothing,1997)中行动与虚无、时间与空间的张力。而图穷匕见的社会矛盾,以及面临洗牌与颠覆的地缘政治关系,也使我们从种族身份、地区、公共与私人空间的边界中体会到一些新的含义。埃利斯在一段九个月前的视频采访中说:“尽管19世纪晚期后,经济与交流渐趋全球化,护照的出现也鼓励人们去更远的地方旅行,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阻碍’与‘限制’。这是这两种现象的错置。”全球化引致了疫情的扩散危机,而扩散的疫情又反制了全球化,正体现了艺术家所关注的这种“错置”。大馆的展览始于人类世的这个关键节点,香港乃至全球多数国家尚未完全摆脱新冠疫情的阴影,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时代语境下,埃利斯的创作也孕育着一种对当下的反思。
行动在未来:以孩童为延续

弗朗西斯·埃利斯,《儿童游戏》,1999年至今,摄影:关尚智
在大馆的对谈现场,弗朗西斯·埃利斯笑着说:“在早期的项目中,我是我大部分影像的主角,但是我的后期作品则大多数以儿童作为主角。我想这是年纪大了的一种自然现象。”对于一个擅用隐喻来创造寓言的艺术家而言,儿童无疑是最为出彩的创作对象。
香港是他1999年持续至今的项目《儿童游戏》(Children’s Game)的最新一站。在这个系列中,他拍摄了世界各地儿童的游戏片段,其中有墨西哥城的孩子在街头用简陋的树枝玩“枪战“游戏,或是伊拉克难民营里的孩子跳飞机等等。摩洛哥丹吉尔的孩子们用鹅卵石打水漂的游戏令他联想到一种对接触天际线的渴望,他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隐喻,最终引向《遇河之前莫过桥》(Don't Cross the Bridge Before You Get to the River,2008)的创作——录像中,孩子们拿着拖鞋做的模型船由西班牙和摩洛哥分别走进海中,跨越直布罗陀海峡,他们嬉笑打闹,用纯真消解了严肃。
在信息科技时代,街头游戏多被电子游戏所取代,孩子们创造规则并游戏于规则之间的本能显得更加可贵。埃利斯着迷于孩子身上的一种与生俱来然而在成长中渐渐磨灭的“透明性”,这种“透明性”指向他所追求的真实和在场,尤其反映于录像这个他最为常用的媒介之一。埃利斯说:“儿童成为我探索一个新地点的切入点,他们使我更容易跟在地人建立初始联系并理解当地的文化符码。尤其是当我拿出摄像机进行拍摄的时候,这个举动会激发孩子们立刻做出不同的反应。”

“每个情况都有各自的特殊性: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边界,基本上是欧洲与非洲的问题;美国和墨西哥,又是另一问题。实际上,我的伊拉克项目并没有实际‘边界’的问题,它是关于历史上殖民力量如何分化、交换,一个原为同一整体的领地;这其实并不算‘领地’,它的游牧居民并无‘领地’概念,只有‘根’的意识。”埃利斯曾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时说,“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 ‘地理’不同。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任何的解决方式。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的工作主要是揭示特定情形的荒谬,并在这基础上建构某种寓言。我试图去嘲讽这些情形,比如,全球经济的流通与当下政策对人口流动限制的反差。当商品流动范围越来越全球化,人们自身情况却并非如此。每个项目,我都尝试把他们重新设定在自己的框架内,因为没有重复的情形。”

弗朗西斯·埃利斯,《卷/回卷》(Reel/Unreel),2011年,影像静帧
在埃利斯2011年所拍摄的纪录片《卷/回卷》(Reel/Unreel)中,阿富汗喀布尔的儿童用木棍推着电影胶片的卷轴玩乐,就如同滚动铁圈一样。他在展览开幕的对谈中说,在那个时期,他某种程度上想借用这个“游戏”来解决自身陷入的一种创作录像的危机,去思考如何处理自己与影像的关系。尤其是当互联网成为联结社群的主要平台,视频串流使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和生产者,每天都有数亿计的视频涌入社交媒体。而埃利斯的作品早在很久以前就被登载于他的个人网站上,并且可供公众任意观看和下载。
当埃利斯看到一些有趣的网络视频时,他也在反思自己的作品之于当下究竟有什么意义,也因此他在《卷/回卷》中延伸出绘画、雕塑、明信片、图纸等其他媒介的创作,通过绘画“在剧组人员没有拍摄的时候与电影保持联系”。他同时也着迷于图像的呈现,试图还原西方媒体报道中所虚构的对阿富汗的想象,让虚构的生活与现实的生活同时上演。但埃利斯的彩条绘画证明,“我发现很难表达阿富汗到底正在经历着什么。要把在这里的体验转译出来并不容易——而且,你会情不自禁地被这个地方和当地的人所吸引,因此这种转译也非常矛盾。”我们可以在他很多作品中见到对两种现象并置的讨论,例如2001年的《重演》(Re-enactments),他把自己购买手枪并在街头游走的真实过程记录下来,又拍摄了一段虚构的剧情,这两条影像被并排放在一起。现实加速了我们对虚拟手段的依赖,我们亦裹挟于无数虚虚实实的信息洪流中,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很难在这个境遇下独善其身时,埃利斯的创作也在激发一些新的联想。


弗朗西斯·埃利斯,《儿童游戏》,1999年至今,摄影:关尚智
对于未来的计划,埃利斯在九个月前的视频访问中透露,他希望自己能够持续和扩延《儿童游戏》系列作品,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亦会更为系统地探索一些尚未被完全开发的新大陆,在那些地方,我们尚能够见到孩子们在街头玩乐。这些孩子们正如同在早期作品中游荡于城市中心的埃利斯一般,无论是在和平或是战乱之地,都能利用最平凡之物和纯真的观察,在被日常生活主导的公共空间内创造想象和隐喻。随着埃利斯创作历程的不断深入,他的行动与在场似乎被延续到了孩童身上——充满蓬勃朝气和无限可能。(撰文/陈谌)
*若无特殊标注
本文图片由大馆当代美术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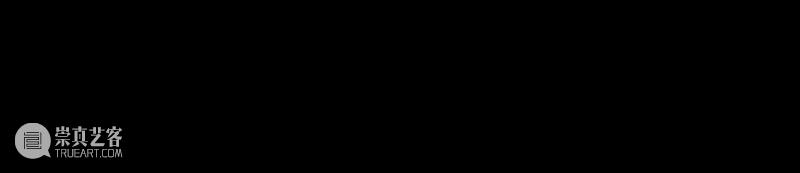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